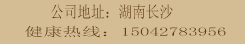物理学家曾经根椐热力学第二定律推导出一个有趣的结论,熵增原理,就是说如果一个系统是孤立的,那么这个系统的无序程度会不停的增加,直到增加到一个最大值,至此这个系统就无法在复杂程度上产生任何变化,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个系统已经死亡。
直接理解熵增原理对于普通人会有难度,但如果换一种说法来解释,熵增原理就很容易被接受:如果你把一滴墨水滴在一杯清水里,那么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墨水会在清水中慢慢散开,清水会慢慢变成黑水,而且这个变化永远不可逆,因此你最终会得到一杯黑水,此时这杯水的浑浊程度不再会有任何变化,它即无法变得更黑,也不会变得更清,当然更不可能返回初始状态,变成一杯清水和一滴孤零零的墨水。熵增原理就是说在这整个过程中,水的浑浊程度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从纯数学的角度来看,“热寂说”是一种物理上的必然,但是在现实的宏观世界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个理论仍然有效吗?当一个文明无法受到外界的影响,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时,这个文明是否会进入一种热寂状态,社会发展停滞,社会结构固化,人口停止增长?如果会,那么究竟是由于社会发展程度达到了环境资源决定的上限,还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原因所致呢?
这个问题并非毫无意义,毕竟从整个地球来看,人类文明从整体上可以视为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地球文明,几乎就是一个物理学意义上的孤立系统(当然,我们可以从太阳上得到阳光,这导致这个系统不够完全孤立,但我们可以将地球文明扩展到太阳系,那么这个文明就几乎完全孤立了)。当然人们可以说,地球文明彻底整合成为一个文明还是很遥远的事情,现在就担心未免杞人忧天。但如果就目前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长年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结构近似固化,人口停止增长,可以说已经接近处于停滞状态(尽管他们并非完全孤立的文明),因此讨论这个问题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检验这个假设的最好办法无疑是看看孤立文明是否有表现出发展的停滞。当然,从微观的角度来讲,文明很难是一个孤立的系统,从物质方面讲,人类需要从周围环境获得能量或者原材料,一个无法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文明显然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构成文明单位的人可能通过战争或者婚姻的方式和其他文明进行交流,而且人会思考,有主管能动性,不喜欢被束缚,总有一些冒险家试图突破环境的限制与外界文明进行交流,因此我们无法找到完全孤立的文明系统。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个文明和它所依赖的必须的最小外在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我们就仅仅需要寻找哪些无法和其他文明进行文化交流的孤立文明作为测试样本。
而且如果肯我们再放宽一下我们的条件,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近似孤立的文明。首先,文明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很容易屈服于环境的压力,尤其是在古代,高山与大海都很容易使一些文明处于一种近乎与世隔绝的状态。尤其是考虑到古代智人在占领了一些岛屿之后可能由于地质条件变化从而无法再回到以前的大陆,因此会在几百年的时间内与世隔绝,而变得与其他文明在文化上彻底隔离,如果把这些岛屿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则几乎是与外界没有交流的。在这方面,波利尼西亚群岛简直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其中的有些岛屿甚至和其他岛屿也长期无法进行交流,成为完美的文明观测样本。至于其他地区,考虑到有些地方可能受到高原或者戈壁阻滞,我们也完全有希望找到一些近似孤立的文明样本。
样本确定完后,我们就需要找到一个指标来判断文明的繁荣程度,或者说,我们需要找到社会学里面的“熵”的定义,从而用于判断一个文明究竟是相对以前更加进步还是已经出现了停滞,有或者出现了倒退。常见的用于衡量文明进步程度的指标,如大型建筑的数量,人口的数量,掌握的科学技艺的程度,可以利用的能量来源及多寡,等等这些指标似乎都各有各的缺陷。但是由于我们的目的是判断文明究竟是否停滞发展,所以我们只要考虑我们采用的指标是否在长时间内保持不变就足够了。至于具体的指标,我们会尽量使用约瑟夫泰恩特提出的社会复杂程度这个指标,因为这个指标从含义上最接近物理学“熵”的定义,而且按照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观点,社会分工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我们也会考虑拿人口作为一个参照,虽然当人口减少时通常社会分工程度也会相应减少,因此这个指标和社会复杂程度指标在某种意义上是重复的,但人口毕竟是一个更加容易参考的目标,而社会复杂程度有时却无法客观衡量,因此,我们尽量同时考虑这两个指标。
我们先观察一下接近孤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文明作为我们的观察对象。
一个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观点是:掌握了当时最新黑科技——独木舟的具有冒险精神的原始人有可能在年前就开始移民波利尼西亚群岛,当然由于海平面上升,他们的后世子孙很有可能再也没有离开过,而著名的复活节岛则至少在年前被人定居。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复活节岛最有意义,因为这个岛极有可能在几百年间甚至没有和其他岛屿上的人有交流,尽管他们的语言和DNA都显示他们属于波利尼西亚群岛文明。
复活节岛显然曾经经历过文明的辉煌时期,复活节岛上残存了座石像,大部分有5米高,最高的石像有21米,最重的石像有87吨,想象一下雕刻并将这些石像矗立起来需要多少人力,而复活节岛上的早期人类居然还需要将这些10吨到90吨的庞然大物从采石场搬到指定的地方(放立石像的地方叫阿胡),最远的路程长达14公里。由于岛民没有轮子,没有牛这样的畜力可以借用,因此这一切全部依靠人力。考虑到岛民甚至可能没有金属工具,你就可以想象这个文明繁盛时的场景,人们估计复活节岛最少曾经有人,人口高峰则可能有15,人,甚至3万人。为了供养这么多人口,岛民发展出了集约农业,采用石块护田法来增加粮食产量,依靠航海技术岛民还会出海捕杀海豚来补充蛋白质。
然而当外界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文明发展早已停滞,甚至可以说是倒退。最早有记录时的估算人口大约有2人,当然考虑到这个时候复活节岛已经和外界文明接触,这个数据很难用于评测这个文明已经衰落。但是有证据表明公元年之后再也没石像被立起,甚至有一些石像是在没有完工的情况下就被抛弃了,静静的躺在采石场。
至于岛民的生活状态,由于大型树木被砍伐殆尽,因此岛民缺乏木材来生火,以前的火葬改为土葬,更无法制造独木舟,航海能力萎缩,无法捕获海豚这样的大型动物,食物来源减少。更糟糕的是,树木减少进一步导致土壤流失,粮食产量开始下降,出现食物短缺,岛民甚至一度出现食人现象。作为社会统治阶层的祭祀和酋长成为灾荒的替罪羊,并在最终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曾经被视做部落权力象征的石像这时就不仅仅是被遗弃了,人们开始推倒其他部落竖立起来的石像,并尽量使其他部落的石像破裂。
复活节岛文明相对于曾经的巅峰时期无疑发生了衰退:由于政变,整个社会在组织架构上变得简单(所有的早期文明都曾经有过祭祀这样的社会层级,而且通常处于社会的顶层,并最终进化成知识分子阶层),尽管这看起来是当时更优的社会选择;人口数量上我们无法准确判断(相对于巅峰期很有可能下降,但无法确证)。但复活节岛被发现时岛民的生活条件显然不是历史上最好的,曾经的金枪鱼,海豚和海龟不再出现在食谱上,后期竖立起来的石像的面部也相对廋削,从骨冢发掘出来的食物残骸来看,岛民的食物来源至少在种类上出现下降。
复活节岛算是波利尼西亚文明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岛民极难与其他岛上的居民进行交流,而整个波利尼西亚群岛作为一个整体显然也很难和位于欧亚非的文明中心进行交流,他们甚至无法和美洲的文明中心进行交流。在外界发现这个文明群体前,整个波利尼西亚群岛普遍出现了文明发展停滞的现象,甚至有些小岛出现了倒退:缺乏食物甚至导致一些岛屿上发生连下葬的死人的蛋白质都不放过的情景,汉德森岛和皮特凯恩岛上的人甚至因为缺乏独木舟作为撤退手段而最终灭绝。用汤因比的话说,波利尼西亚文明的先祖们发展出了超能力,在攀登文明高峰时,他们成功的爬上了一块凸石,但这块凸石远离其他落脚点,以致于他们无法继续向上攀登,因此在丧失了自己的超能力后即无法后退,也无法前行,只能待在原地。
波利尼西亚群岛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几乎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文明,基本符合物理学关于孤立系统的要求。在天才般的航海技术帮助下,岛民的先祖把自己送进了一个方外之地,并在这里发展出自己的文明,部分岛民搭建的石像至今令人惊叹,因此我们不必怀疑岛民的平均智力水平,但是显然这个文明最终进入了一种热寂状态,文明无法向前继续发展,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
但是如果我们将复活节岛的岛民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割裂去分析,那么我们将得到一个没有意义而且几乎是显然的结论:由于环境可以稳定获得的能量来源近乎固定,所以岛民所能发展到的文明等级必然会停留在一个维持可持续发展的阶段,这种限制是一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岛民不可能打破这种限制,岛民对这种客观限制无能为力。而且波利尼西亚群岛都是火山岛或者珊瑚岛,因此缺乏金属,有些岛屿甚至缺乏石头这种文明发展所必须的资源,所以波利尼西亚文明发展到一个停滞阶段是必然现象。
但是如果把复活节岛岛民和它所处的环境结合在一起来看,我们就会去问:岛民是否有可能通过提高技艺水平从而让同样的环境提供更多的食物来源呢?又或者拓宽他们能够有效利用的环境范围呢?
前者确实是可能的,科技进步在复活节岛上是存在的,岛民发明了“石块护根法”来提升农作物的产量,从而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但是也仅仅到此为止,岛民没有发明出更高效的利用环境资源的方法,也没能发展出比独木舟更高科技的航海手段来拓展生活范围,原因可能是缺乏发明更高效方法的资源,也可能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或者两者都不具备。
但考虑到搬运石像需要砍大量的树木用于制作滚木或者绳索,而如果将这些资源节约下来,那么水土流失和缺少独木舟就可能不会发生,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岛民曾经拥有多余的资源可以投资在对于文明发展更重要的地方,比如智力投资上,最不济岛民也可以像新几内亚人那样将资源投资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这样他们的文明至少也可以维持可持续发展”,然而岛民却没有这样做。
这样明显的失误究竟是环境上限造成的,还是文明本身的特征造成的呢?考虑到后期被发现时岛民甚至连灌木丛都不放过(可以用来覆盖屋顶或者生火),我认为人性很可能给波利尼西亚文明限定了一个更低的文明等级。
当然,这个结论也还有一定的逻辑缺陷,因为波利尼西亚群岛四周是广袤的太平洋,所以岛民不论怎么努力拓宽环境范围可能也只能得到更多的海水,却很难大量得到文明发展需要的金属,木头与石头,而由于地质原因他们也几乎不可能再回到大陆(虽然复活节岛已经靠近南美洲相对很近,但也有公里,距离自己最近的皮特凯恩岛则有公里,他们曾经的航海技术可见一斑);而提升科技水平则需要大量的投资和人口基数,复活节岛最鼎盛的时期也不太可能超过3万人,而岛上的物质条件显然无法支持这样科技发展,而且这些岛屿相互之间进行文化和技术交流都有现实的难度,因此各岛上的人口数量几乎就可以视为各岛屿的人才基础。考虑到天才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是稀缺资源,因此通过岛民自身的智力来发展文明完全可能是一种奢望,所以即便岛民把相互争斗,竖立石像的资源用在教育上,他们也没有可能发展他们的文明,因此很有可能这种人性本身定义的天花板其实还是某种意义上由环境决定的。或者说并非岛民不够聪明,而是他们纯粹倒霉,那么如果让这个岛屿再大一些,他们的悲剧是否就可以避免呢?
让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文明,一个更容易获得各种资源,一个人口更多,但缺乏与其他文明交流但内部交流频繁,而且智商似乎更高的文明,玛雅文明:
按照现代的估测,玛雅文明鼎盛时期可能有万人口,这个人口数量即便是在今天,也可以称为一个国家,我们无从判断玛雅文明中盛产天才的比例,但是玛雅人发明了数字0,并且发明了20进制,至少从数学上来看,玛雅人很有智慧。与波利尼西亚文明一样,玛雅人留下了震撼人心的文明成果,埃尔米拉多尔的旦达金字塔如果第一层不被算作底座的话就是世界最大的金字塔,即便是当做底座处理,也是全球第十大金字塔。
但是玛雅文明也是一个近乎与其他文明隔绝的文明,玛雅人所处的地方一年大部分时间气候比较潮湿,这就导致他们的主要食物,玉米,无法长期储存,而且玛雅人没有用于运输的牲畜,也没有轮子用于辅助运输,运输主要靠人力,由于缺乏食物保存技术和高效的运输工具,玛雅人很难与外界文明进行交流,事实上玛雅文明要到16世纪才与外界文明产生有据可查的接触(当然这时他们的文明已经衰落)。
但正由于缺乏有效的运输方式,玛雅文明无法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帝国,整个文明采用城邦制,结果各国王征战不断,因此玛雅文明拥有比波利尼西亚群岛更多的内部交流机会。从结构上看,各城邦的国王兼任祭祀,同时也存在贵族和农民,因此社会的等级结构与大多数古文明相同。
虽然关于玛雅文明的文献记载极少,但是从结果上来看玛雅文明已经不仅仅是发展停滞了,如果以人口数来衡量,玛雅可以说出现了严重倒退,公元年左右,埃尔米拉多尔被荒废,公元年后,玛雅文明90%~99%的人口消失,佩腾中部地区的人口从巅峰时期的大约到1千4百万人最终下降到西班牙人发现时的3万人。考虑到玛雅社会采用城邦制,我们无法从人口数量下降必然判断玛雅社会的复杂程度有降低,但是科潘的国王被推翻,王宫被烧毁有可能意味着社会层级的减少(贵族阶层依然存在)。
现代人将玛雅文明的崩溃归结于内部战争和外部气候干旱,对于一个几乎无法与外界文明进行沟通的文明来说,这应该是惟二的原因了。但是一个文明的内部战争本来就是这个文明的成员的自发选择,因此如果是内部战争导致玛雅文明停滞,那么这并不会改变我们的结论。何况玛雅文明各城邦所处环境的同质性很强,食物又无法长期存储,那么干旱爆发时就导致所有的城邦同时缺粮,既然无法互通有无,自然只能采取战争这种极端方式来解决食物问题。
干旱有可能是很大的原因,但是环境变化是一个所有文明都会面临的问题,文明存在的前体就是适应环境,而非被环境淘汰,如果真是因为干旱导致玛雅文明衰退的话,我们只能说玛雅文明缺乏弹性。而且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衰减,并且衰减在之后在近1千年内都没能恢复人口数量和文化,这未免令人深思,而且现代的考古分析也只表明曾经发生过短期的连续干旱(最长10年,虽然很长但玛雅的很多城市被废弃长达几百年)。
而且玛雅文明有自己的文字,他们完全有能力记录下旱灾的历史和应对建议供后人参考,换句话说公元年的严重6年旱灾完全应该有应对方案,因为此前曾经发生过更严重的10年旱灾。何况玛雅人自己构建的储水池显示他们也知道自己需要做这方面的准备,提卡尔城的储水池可以存储足够1万人1年半的用水量。
显然玛雅文明没有发展到外界环境所能决定的上限就发展停滞,甚至出现了衰退。这种发展停滞极有可能是和人类文明自身的特性而非环境决定的。
当然,由于缺乏文献方面的证据(感谢主教迪亚格德兰德),我们也许可以猜测:虽然玛雅文明某些地区的人口确实下降了很多,但是很有可能这些聪明人逃难到其他地区,而且因为这些地方更容易生存因而不必回到最初的文明中心地带。确实,在玛雅人口减少的同时,尤卡坦的人口迅速增加,虽然尤卡坦的文化本质上是玛雅文明的继承,而且复兴后的尤卡坦的文明程度和之前玛雅文化全盛时期的状况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其他逃难的人有可能有了更好的发展,只是我们并不知道,或者他们的成果另有特色,因此被冠以全新的名字,比如阿兹特克文明。虽然这个可能性很低,还不能解释为什么玛雅人放着已经建设好的家园不回,偏要跑到更冷的北方重新开始?但这确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可能性,而且不得不承认,阿兹特克文明确实和玛雅文明有一些相似性。
当然这个可能性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结论,因为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本质上是两种文明,而且玛雅人也并没有灭绝,但他们先祖修建的雄大建筑却隐藏在森林里,不为人知晓,因此玛雅文明毫无疑问是停滞了。但我们仍将继续我们的寻找,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很难与其他文明发生联系,同时又要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个文明不曾中途迁徙或者变异成另外一个文明,当然,这个文明必须要有足够的人口基数,确保这个文明可以产生足够多的天才来杜绝“缺乏人才因而被迫停滞发展”的悲剧。当然,通常来说一个文明人口越大,就越容易与其他文明产生交流,波利尼西亚文明人口少,又蛰居在太平洋的小岛上,是一个孤立系统的近乎完美样本,但一个人口众多的文明就很难不和其他文明产生交流,但是我们也许可以从一个文明的身上切出一个片段来做单独的研究,因此让我们把目光转回东方。
从地理位置上讲,日本与欧亚文明中心的距离不是很远,使他能够吸收来自中国文明的成果,并间接受到欧洲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影响,但是日本与欧亚大陆架的距离又远到使他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所以虽然日本文明是中国文明的子文明,但是这个文明可以自主选择对待其他文明的态度,而从“禁教令”到“黑船事件”期间的日本江户时代就是一个近乎与其他文明割裂的时代。
在丰臣秀吉的“二十六圣人事件”之后,继任者德川家康进一步强化了禁教令,日本进入锁国状态,在官方合法方式内,日本只能与中国和荷兰进行文化与商业上的交易,这种锁国政策短时间内稳定了幕府的统治,江户时代日本的社会结构最终稳定为将军,武士和农民(商人属于附属阶层)。
从织田信长到丰臣秀吉一统日本之前,日本长期处于战乱状态,因此统一后的日本人口迅速增加,德川幕府初期日本有万人口,但亨保改革后日本人口一度增长到万左右,然而在江户时代中期人口数量停止增长,并且在18世纪末期开始出现减少,最低至万人以下,虽然官方的数据可能有统计问题,但是人口数量持平甚至减小是不争的事实。日本的社会结构在这段时间之内并未发生大的变化,武士阶层确实有分化,但是这种分化似乎更多的是一种官职等级,而且类似的等级在德川幕府之前的镰仓幕府时期也同样存在。
在江户后期,普通日本人的生活极其艰难,米价就是最好的避孕药,普通人被迫采取“间引”和堕胎的方式来维持生活水平,天明饥馑更是造成接近1百万的非正常人口减少,民间甚至出现杀妻弑子的现象。日本人口在年为人,年江户幕府最后一次调查时为人,日本人口在年内仅仅增加了84万人。而且由于“间引”被大量采用,政府被迫出台法令来禁止,但是弑婴现象仍然无法杜绝。
年“黑船事件”打开日本国门,日本文明的孤立程度大幅降低,日本文明也随后进入明治时代,但江户的后期,日本文明极大概率陷入了发展停滞,虽然期间有人口减少,但是由于锁国政策,所以不曾发生大规模的外部殖民;而为了解决大面积的饥荒,松平定信采用抑商政策,资本主义萌芽被掐断,商人没有能够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日本的社会结构没有能够发生变化。
年明治政府首次进行人口普查,日本人口为人,在26年内日本人口增加万,增长23%。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显然不可能是由于在26年内发生了科技的显著进步,而应该理解为日本的环境资源结合日本当时的技术水平确实可以支撑更多的人口数量,但是江户时代,文明的发展被某种非环境相关的因素抑制了,因此人口被迫维持在一个更低的水平上。
当然,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更多的近似孤立的文明样本,新几内亚高地文明也是一个几乎完全孤立的文明样本,这个文明进入了一个近乎不可打破的停滞状态,其经济组织方式更像计划经济,甚至具体到每一颗树是否可以砍伐,什么时间点砍伐都有例可循。虽然岛民如果能够稍微努力一下,他们就会发现澳大利亚并极大拓宽他们的生活环境,但是他们选择把自己封死在森林里,通过弑婴,堕胎和禁欲的方式来控制人口数量,这种方式虽然比蒂科皮亚岛上自杀的方式强一些(投海或者上吊都有),但显然也没有强太多,而且这无疑表明这个文明的发展陷入了停滞。
但无论我们找到多少例子,如果我们无法找到背后的原因,那么我们的猜测就依然是猜测,只不过多了一些例证而已。假如文明的发展上限除了受环境制约之外还受文明社会本身特性的制约,那么这样的制约机制会是怎样的呢?
物理学中的熵增原理针对的必须是孤立系统,如果一个系统能够从外界得到帮助,比如有人不停的对脏水就行过滤,那么这个系统的熵确实有可能减少。类似地,斯塔夫·里阿诺夫也指出,一个不方便与其他文明进行交流的文明在发展上会落后于那些更容易与其他文明交流的文明。这可能是由于其他的文明可能会带来更新的技术,更先进的体制,又或者是由于外部竞争为文明的进步提供了元动力,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显然不能将自身文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老师,或者能够有一个外部敌人身上。
忽略外部的影响之后,我们能否从文明的内部找到一些机制呢?熵增原理是基于一些热力学机理不可逆作为基础的,墨水在不被外界干扰的情况下一定会将整杯水污染,这个过程不可逆,那么社会学里面有没有一些机制是不可逆的呢?
约瑟夫泰恩特指出边际收益递减是社会学里一个几乎不可逆的过程,当社会的复杂程度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任何复杂程度的提升,不论是技术的还是制度的都需要付出昂贵的成本。今天随便一种新药的研发成本都远高于青霉素的发明成本,小孩养育成本和教育成本甚至让很多中产家庭望而却步。今天的制度变革成本不仅远超以前,而且很多时候根本不可能发生:澳大利亚直到今天还在出口羊毛,矿石这样的初级产品;俄罗斯的改革到现在也还没有成功的迹象;1百年过去了,土耳其的世俗化政权仍然面临威胁。而如果没有黑船事件和鸦片战争,德川幕府和清朝的部族统治都会持续巩固。
逻辑上推理,边际收益递减和边际成本上升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发展到一个收益和成本等值的一个临界点。亚历山大在将边界拓展到印度的时候,政府对国土的控制力早就达到了当时信息传输技术所能支撑的临界点,接下来的分裂是一种必然选择;当罗马帝国征服四方,它的财务状况也到达了现金流量和负债之间所能支撑的临界点,于是接下来的大规模通货膨胀也成为顺利成章的必然选择,货币贬值成为整个帝国存续期内的主旋律,东罗马帝国之所以能够比西罗马帝国幸存更久,也仅仅是由于东罗马帝国控制着更有价值的贸易路线,因此财务状况更佳而已。
但是这种平衡从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理解为外界环境限制的一种变体:正是由于铁矿石在澳大利亚的丰度很高,成本便宜,所以虽然澳大利亚是一个发达国家,但依然可以靠销售铁矿石,甚至销售羊毛和原木谋生,因此澳大利亚必然在高科技领域乏善可陈。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文明通过外界环境获得能源的成本如果很低,那么显然该文明在任何技术领域的研发成本都会降低,从而改变收益平衡的临界点,因此这种边际收益和成本导致的临界点本质上仍然是由于环境因素制约的。
那么除了经济学上的边际收益递减,是否能够社会学领域找到其他的不可逆机制呢?
回到日本的例子里,我们很容易发现一种社会学里不可逆的机制,马太效应。事实上整个江户时期日本的粮食产量都是保持增长的,从整体上来看,日本人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升,但马太效应使得普通农民的生活质量没有大幅提升,由于地租构成从四公六私发展到后期的七公三私,上涨率超过70%,普通人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从而缺乏足够的资源投资新的生产技艺,也就无从掌握更多的资源。继承了丰臣秀吉统治技巧的德川家族也致力于削弱各国地方势力(这里的各国是指日本各地方行政区域),因此幕府的统治越来越牢不可摧,强者恒强,弱者更弱,从木下藤吉郎到羽柴秀吉的转变越来越不可能在普通人中出现,社会结构趋于固化。
私有制诞生后,资本相对于劳动在盈利中的获取比重日趋增大,只要在和平年代且没有大规模瘟疫的情况下,财富集中度都越趋越高,伴随着人类从食物采集者进化到食物生产者,人与人之间财富的差距越来越大。
人类文明基尼系数随时代的变化[2]
不患寡而患不均,马太效应一方面激励人取得成功,极大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财富分化,成功导致更大的成功,因而既得利益者反而可以利用自身的资源来限制社会进步,成为阻滞社会进步的最大阻力。在大航海时代大放异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殖民新大陆和垄断海上贸易攫取了巨额财富,然而这些财富反而帮助统治者阻止了可能发生的资本主义革命,因为统治者有更多的资源来维持自身的统治,革命难以成功,从美洲获得的大量白银则大幅提升了工人工资,造成大幅通货膨胀,并最终损伤了实体经济,反而错过了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
究其原因,马太效应是不可逆的,它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超某一个方向倾斜,但是现有的社会里并没有任何机制可以和马太效应对抗。虽然人类发明了税收,但是税率机制显然不能改变私有制的本质,因此很难与马太效应对抗,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巴菲特秘书缴付的税率比巴菲特自己还高。
一个系统的存在需要截然相反的两种机制来维持,而且这两种机制要能够对抗,水杯能够没有跌落在地板上砸成粉碎,是因为地球的引力和桌子的支持力方向截然相反,而大小则正好相等,因此杯子才能既不会像气球一样飘在空中,也不会摔在地上。但是当马太效应持续发展下去,我们的社会则缺乏这样的机制能够对抗财富的集中趋势,杯子被迫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那就是地板,只是此时它已然粉身碎骨。
江户后期,普通人缺乏资源来进行创新,统治者则将资源大量投资在维持自身统治上,并尽一切可能削弱其他阶层所能控制的资源数量(更早的丰臣秀吉甚至通过要求地方藩主定期朝拜但不限制随从数量的方式来消耗藩主的经济实力),同时扼杀所有可能威胁到自身统治的创新。技术进步确有可能,但底层人民的生活几乎没有改善,也没有改善的希望,因此主动或被动控制生育,从人口数量和社会结构的整体来看,日本社会发展陷入停滞。
在私有制的帮助下,马太效应得到了大幅强化,马太效应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无法改变,那么有办法改变私有制和基于私有制的分配方式吗?随着7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社会学试验结束了,马克思的学说在学术界重新被反思。
如果把79年试验的结束视为改变劳动和资本在价值分配中比重的失败尝试,那么目前的社会学里似乎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抗衡马太效应和私有制的组合。
全球化以前,一个文明如果被外来文明强行打破孤立状态还有可能进行改革或者通过革命的方式来强行改变社会结构,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地球文明越来越像一个整体,而作为一个整体地球文明似乎已经进入人口停滞状态:几乎所有的国家妇女生育率都低于替代率(最近印度也决定实施计划生育),日本重新陷入了人口负增长,如果没有移民的帮助,欧洲和美国也必然出现人口负增长。
也许我们可以考虑用技术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确实浆帆两用船大幅改变了底层划桨手的社会地位,如同舰炮的射击方式革新改变了炮手的地位一样,但是从人类进入私有制到今天,所有的技术都优先被用于增强和维持统治上,技术作为一种手段自然更容易被拥有更多资源的统治者利用,这也是马太效应的一种必然。日本在江户时代后期也并非没有技术进步,但人口仍然没有增长。
当杯子碎落在地板上,地板仍然能够为杯子碎片提供支撑力对抗万有引力,但是如果地板的支撑力不足一抗衡引力,那么引力会把杯子碎片连同地板紧紧吸在一起,这个体系永远不可能取得平衡,最终进入一种死亡状态,物理学给这种无法平衡的状态起名叫做“黑洞”。
逻辑上说,任何有一个社会学机制如果无法找到对应的平衡机制,社会都无法长期稳定存在,最终会像“黑洞”一样走向死亡状态。如果无法找到能够对抗马太效应的机制,我们的文明自然会陷入“黑洞”这个陷阱,这也许是费米悖论的一个可能解。
在目前的价值分配体系里,获取收益的要素是风险,资本和劳动。如果我们无法改变资本和劳动在价值分配中的比例变化趋势,也许惟一的方向是走向风险,从未知中寻找突破。
[1],《崩溃》,贾雷德*戴蒙德著,江滢叶臻著,页.
[2],Greaterpost-NeolithicwealthdisparitiesinEurasiathaninNorthAmericaandMesoamerica,TimothyA,Kohler,Nature,,-.缺铜会得白癜风吗福州治疗白癜风的医院转载请注明:http://www.yingluncar.com/gjqh/4548.html